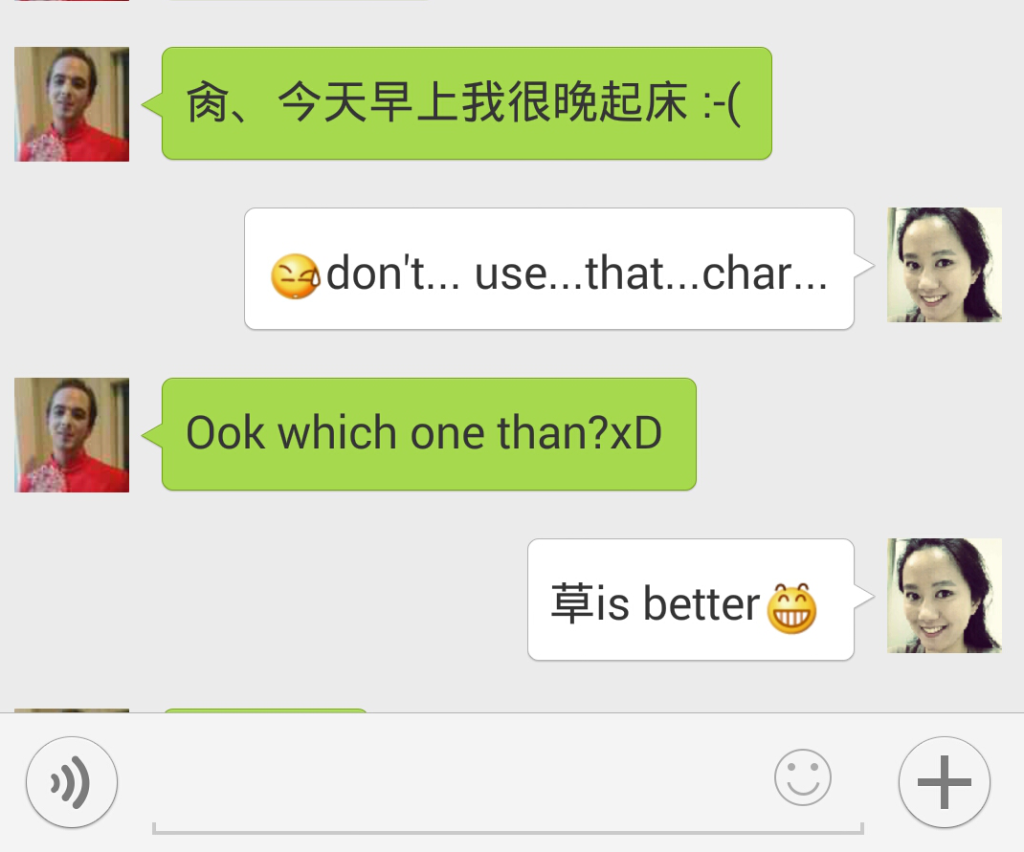事情要從十二三年前說起。五年級的小蛐蛐坐在媽媽自行車後座上,忽然發覺近幾周來自己的咽喉好像有點不受控制。就是在想咽口水的時候,喉嚨好像使不上勁。再過幾周又驚恐地發現,自己開始口吃了。
這一口吃伴隨小蛐蛐八年,從十歲,到十八歲,其中紛繁雜亂的頭緒自不必說,十八歲後偶然有一天發現自己解脫了,心情也並不輕鬆。因為若干年前某一天,知道自己這個不請自來的口吃,和天生的左撇子竟然有莫大關聯。
神經外科醫生保羅·布羅卡(對,你沒聽錯,就是“布羅卡氏區”的布羅卡),他認為腦部技能運用方面,左撇子是右撇子的鏡面影像,也就是說——是反過來的。
這個理論很吸引人,以至於人們一度以為我們左撇子的心臟也是在右邊的。這當然從解剖學就否定了,但大腦運行機制確實和左右手有密切關係。
關於這一點,我沒有找到有力佐證,但想到若干年前看的一篇文章,是說一般人左耳對音樂的感受能力超過右耳,而受過訓練的音樂家剛好相反。
我們知道,左腦負責語言、數位、邏輯以及種種分析性功能,而右腦則支配音樂、藝術類的活動。換句話說左腦是理科生,右腦是文科生。所以我猜測,受過訓練的音樂家將音符化解成了符號性的東西。而據我所知,左撇子的聽力也是和一般人相反的。
如果這還不足以證明左撇子大腦和右撇子成鏡面影響,也許我本人的例子可以做一個補充,就是不僅僅我習慣性使用左手,我還習慣性使用左腿,左腿力量也比右腿力量強一些,這表現在包括踢毽子、踢球等各種活動中。
所以我想,普通人左腦中的布羅卡氏區、韋尼克氏區(甚至現在流行的布羅德曼區理論),大概都正好與左撇子相反。
這就解決了我長久以來的一個疑問,如果左撇子和右撇子大腦運行機制相同,那麼我作為一個左撇子,為何還有如此優秀的語言表達能力(不謙虛地說,從小語文成績在班裡、在學校就所向披靡)。
這裡要說到關於布羅卡氏區、韋尼克氏區。神經語言學家認為,布羅卡氏區負責把語言映射轉化成語音,而韋尼克氏區的功能則是把語音轉化成語言的映射。聽到對方說話然後用語言回答的過程可能是:
1. 聽覺衝動傳至聽覺區,產生聽覺;
2. 聽覺區與韋尼克區聯繫,理解問話的含義;
3. 經過聯絡區的分析、綜合,將資訊傳送到運動性語言中樞;
4. 運動性語言中樞通過與頭面部有關皮質的聯繫,控制唇、舌、喉肌的運動形成語言,回答問題
注:運動性語言中樞,即布羅卡氏區的一部分。
這裡有必要說明的是,目前來講,人們一般認為大腦中負責語言的區域比傳統的布羅卡氏區、韋尼克氏區要大一些。不過這不重要,因為我們不是神經外科專業。
這裡比較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都知道,人一生當中學習語言的黃金階段是一歲半到六歲半。這並非是我們常說的“小孩記憶力都好”,而是因為語言學習的本能只存在於一歲半到六歲半這段時間內。因為小小的人腦卻是消耗能量巨大的東西,要消耗掉人體四分之一的能量,原始人類的小孩長大後不需要考CET考雅思考託福,所以學會母語之後,這種本能就不再有用,與其留著消耗能量,不如讓其衰退。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在幼年時期各個是語言天才時間一過就變成白癡,面對一堆雅思託福淚流滿面。
這裡有個佐證,有個小孩從小不會說話,被醫生診斷為智障,悲催的是,到了三十一歲,才有人發現她是聾的。後來她配了助聽器,學會了很多東西,但就是學不會語法。
類似的證據很多,和世界各地經常報導的狼孩、豬孩類似,他們一旦錯過語言學習時期,就再也無法像別人一樣擁有好像是“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
在這裡還有必要提一下Foxp2基因。提到Foxp2基因之前,還要順便提一個插曲,在筆者參加的一個研習方言的小圈子裡,一個方言牛人曾嘲我是沒有母語的人。因為我已忘記我的合肥方言,作為第二語言的大連方言也快要忘記,作為第“三”語言的上海方言還正在雛形中。而普通話自然不能作為我的母語。這是悲涼的事情,儘管合肥話隸屬北方方言江淮次方言,有降調較多,不如南方方言好聽、有古意,但畢竟也是數萬年來的層層累積,是我的母語。不過後來我又發現又這麼一種人,天生是沒有母語的。就是SLI(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患者。這種病症比較悲慘,雖然患者心智、聽力乃至發音都正常,但天生說話緩慢、吐字不清、語法錯誤連篇。
SLI是由基因決定的疾病,SLI患者的Foxp2基因有了毛病,Foxp2基因,全稱是Forkhead box p2。這個基因在很多動物身上都有,人類的Foxp2基因和大猩猩的只有非常微小的差別,但這微小的差別足以造成天壤之別,這種基因的作用,就是構造一個如簧巧舌,和語法天才的大腦。
其實我們每個衰退了語言學習本能還在每天備戰英語的可憐人,跟SLI也差不多。只是SLI無論年齡大小,都失去這種能力。
所以我們知道,為什麼兒童的語言能力是我們這些秉燭夜戰的人們所不能比的。
wug測試(wug test)是檢驗小孩語法能力的一個好方法:給小孩看一張圖,畫著一個小雞一樣的動物,告訴他/她,這是一個“wug”,然後再給他看另一張有兩個動物的圖,問小孩這是兩個什麼東西。講英語的四歲小孩會回答“wugs”,這證明小孩不是鸚鵡學舌(“wug”是生造的字,小孩不可能聽過別人說“wugs”),而是真正掌握了“複數後面加S”的語法規則。
這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動物也許會學會詞彙,但永遠學不會語法。這裡要說到一個大名鼎鼎的猩猩擰姆猩斯基,是的,你沒聽錯,它的名字就來自於我們尊敬的喬姆斯基。他學過美國手語;還有倭黑猩猩康吉,會用畫有符號的塑膠卡片和科學家交流,以及一直非洲灰鸚鵡,他會說150個單詞,能叫出50個東西的名字。
申小龍的《語言學綱要》裡舉過猩猩的例子,認為猩猩具有一定能“語言”能力,例如名詞性符號概括、動詞性符號概括、符號義引申、符號創制、符號位移、符號組合等能力。但即便是這樣,動物的這種能力,和人類的語言能力也是有根本區別的。具體區別已由上文關於生理機制的部分闡述清楚。
所以我個人認為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於“語法”,而語法即思維,這也是為什麼兒童在詞彙學習上未必比得上大人,但學習語法比大人快很多。這個時候我就萬分同情SLI以及那些因各種腦損傷而失語的患者,思維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花朵,而他們的大腦裡是莽莽草原。我很想知道他們是如何思維的。就像我很想知道一個成年之後到第二語言的環境裡生活幾十年的仲介語使用者,他們的思維是母語,還是第二語言。
這裡就又要說到皮欽語和克裡奧爾語。如果說皮欽語是一種半人造的、缺乏語法的語言的話,那麼克裡奧爾語可以說是皮欽語的孩子,繼承了亂七八糟的詞彙,和天賦的語言本能。即克裡奧爾語基本上可以說是洋涇浜語言使用者的小孩,他們在一歲到六歲之間自己總結出了屬於自己的語法,就成了成熟的克里爾奧爾語。
當然,我們知道,還有人造語,諸如“愛斯不難讀”,甚至還有納美語之類的,創造語法真是一件難事,人們如何站在自己的思維上創造另一種思維?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很有意思,叫做《天下第一句:要有光》,這篇文章很短,我且摘下來:
瑞典語言學家及非洲語言專家簡森(Tore Janson)在他的《說話:語言簡史》(Speak: A Short Historyof Language,2002年)中提到這麼一個現象,作為解釋世界由來的權威之一的《聖經》,沒有提到語言是怎麼來的,亞當生來就會說話,給動植物起了名字。在亞當之前,只有一個東西會說話,那就是神自己。
神說:“要有光。”。。。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神說。。。(《聖經·創世紀》)
簡森提到的現象透露給我們一個資訊,那就是,語言之於人類已經到了多麼分不可分、想不可想的地步,以至於當年編寫《聖經》的人們千慮一疏,竟然忘記讓神來創造語言了。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創神者們用以區分人類和動物的標準。人天生會說話,跟上帝一樣,動物不會說話。人類之謂人類,在於會說話。這不僅是創神者們的觀點,也是很多人類學家及語言學家的觀點。自從人類掌握語言能力之後,就離開了動物,開始了人類自己的歷史。
可是,到了伊甸園裡,情況又不同了。原來蛇蠍也會說話,而且蛇蠍說的是人話,否則夏娃是聽不懂的。如果夏娃沒聽懂,也就不會有我們這些生來要受苦受難的眾生了。
換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最初的人話和動物的語言沒什麼區別。推而理之,上帝說的也是人話,或跟動物類似的話。
這樣一推理,原來上帝、人祖、動物說一種語言,大家其實沒有多大區別,因為《聖經·創世紀》沒有提到翻譯現象,大家都是當面直說,頂多是神躲在暗處說話,不打照面而已。這件“事實”,卻從來沒有被信神的人類學家或語言學家引述過。因為它所揭示的是,人之為人,與語言無關。人能說的,動物也能說。甚至在語言方面,連上帝都沒有什麼特殊的,上帝能說的,人和動物都能說。
神說:“要有光。”
這話,人還聽得懂,但動物怎樣也是聽不懂了。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據,證明達爾文的進化論是錯誤的,起碼在語言方面不能應用達爾文的進化論,因為動物的語言能力明顯不如當初了。就是打死蛇蠍,他們也不會說一句人話了。
語言能力的退化,對動物來說,是件很值得悲哀的事。不過,這也只是人以為值得悲哀。作為整個動物這個群體來說,也許無所謂。也許他們不以為是退化,反而以為是進化,因為他們早已掌握了他們自己的語言,人類聽不懂了。這也許是件快事。有時就發現說其他語言的人在大庭廣眾中一起用別人聽不懂的話竊竊私語,就有一種很享受的優越感。
上帝出現在《聖經》裡之前是否會說話,說了什麼,《聖經》沒記載或描述,我們無從知道。既然“要有光”是神在開天闢地之初的話,按照中國人歷來喜歡標榜天下第一的習慣,這句話實該被封為“天下第一句”。不過,這個天下比我們自以為的天下要大許多。
看到這裡我忍不住嘲笑一下,啊,原來這傳說中的天下第一句,竟然還是個無主句。眾所周知,我最愛無主句。
但這裡緊接著又衍伸出兩個疑問,第一是人類如何站在語言之上研究語言。這實在太難了,因為人們的世界歸根結底是語言的世界,人們無法穿越語言去觸摸世界。每個人的世界都在他接受語言的概念的時候就悄悄建立起來了。第二個問題是,啊,終於要回到我目前的專業了——第二語言習得者,如何在沒有語言學習本能的説明順利習得第二語言,像兒童那樣?還有就是,因為外語學習越來越重要,人類最終會不會進化出永不退化的語言學習本能呢?
而我的觀點是,即便語言學習本能消失,但作為人類,我們仍然具有無可匹敵的符號創造、辨識能力,以及對規律的歸納、演繹能力,運用這種能力,我們或可彌補語言本能衰退的損失。這也是為什麼仍舊存在大量成年的優秀二語習得者。
還有就是,我覺得,語言能力和符號辨識、創造能力以及對規律的歸納演繹能力並非是有截然的分界線的,他們之間或許有著相融共通之處。就如雖然我們脫離語言就無法思考,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去享受語言無法表達的音樂、藝術,他們也是一種類似“語言”的符號,用來溝通世界與心靈,而顯而易見的,他們不是語言。當然,我也不確定,這種非語言符號的感受能力,在語言學習本能衰退之後,他們是否也同時衰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只能說,我們對布羅卡氏區和韋尼克氏區的理解僅僅局限在了語言方面。又或者說,是否我們對語言的概念太過狹隘。我們是否可以將一切思維都視為語言,將一切思維方式都視為語法?就像電腦有電腦的語言,數學家有數學的思維。
大概事實也是如此樂觀的,否則我們這些已經成年的二語習得者學習起第二語言來,未免太過希望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