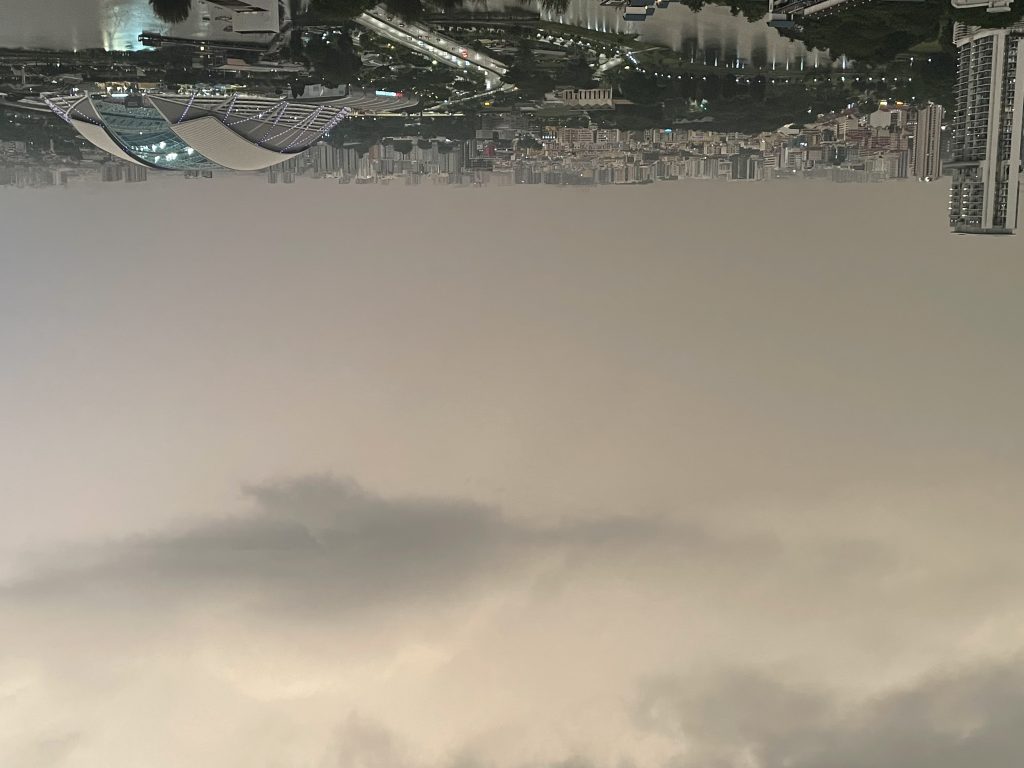据说甘榜格南斋月巴扎和芽笼士乃斋月巴扎齐名,是新加坡两个最大的斋月巴扎之一。我地图上一查,嘿,这不就在我家旁边。住处附近的阿拉伯街算是旅游区,刚来的时候有天肚子饿,看到黎巴嫩餐厅就高高兴兴坐下吃了个烤肉+米饭,味道是好,但25块钱的价格让我十分肉痛。后来当地人和我说,那里游客多,价格自然贵,换别的地方也就十来块。这块区域除了苏丹回教堂之外另有两座小清真寺,白天和夜晚不定时常有从各个寺里传出的唱经声。唱经声伴随我度过了很多看月亮的夜晚。

斋月期间我下班常路过那里的巴扎,一条街亮了一排灯,人群或排队或立在街边,影影绰绰,能闻到食物香气。我暗暗握拳告诉自己把持住,等周末了就过来吃。
但不得不说,斋月巴扎的开饭时间对我这种下午两三点之后就逐渐少吃不吃的人实在太不友好了。前天good friday,和朋友们去岛上浪了一圈回家路过甘榜格南巴扎,五六点钟,wah lau eh,I tell you ah,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ah!外面排了百来人的队伍(顶着北纬1°的太阳,没有遮阳棚),进了里面每个stall还有虬曲的长队,热爱巴扎如我也毫不犹豫就吓跑了,跑去旁边小摊吃了碗卤面回家睡觉去了。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我特地早去,一点多就去了,果然没人排队——因为还没开。大家正忙着准备工作,卖汉堡摊子的小哥正在一人高的蛋堆里疯狂敲蛋搅蛋。只有一个kebab的摊子勉强转起了烤鸡肉,秉“来都来了”原则的我买了一个鸡肉kebab,味道远逊geylang serai那家——我最近鸡肉浓度过高因为鸡肉便宜——非常伤心地又去旁边小摊吃了碗laksa。今天周日,我还有一次机会,决定说什么也要等到三点。结果是十一点半我就饿了,公司楼下food court找了个kebab小stall吃了份Dominik Doner流着眼泪不甘心地吃了,味道当然是很好的,但就是不甘心。不知道一会儿还有没有胃再去一次bazaar。

胃当然还是有的。两三点多开始下起雨来,我回去拿伞就晚了,但心里也笃定些,下雨人肯定不会多。过去一看果然,外面居然没有排队,里面各个stall前面排着几个不成气候的小队。和芽笼士乃不同,这里的巴扎只有一个单排,对面还是正常营业的门面,中间用护栏隔开,西边入口东边出口。移动的人群形成洋流,这头进来那边出去,很难走回头路。




这里的巴扎没有geylang serai那么多signature的食物,但是ramly burger还是有,昨天看到小哥在蛋堆里疯狂搅蛋的,原来准备的就是ramly burger的食材。很多当地人推荐ramly burger,说那是最好吃的burger。甚至有当地人说只有马来西亚的ramly burger才是真正的ramly burger,因为新加坡当地的ramly burger并没有用到马来西亚的牛肉原材料。我当然不信那会是最好吃的burger,我甚至不相信它会好吃。但既然大家都推荐,我还是要尝一尝。




饮品摊子大多没什么人排队,还有些没名气的小摊子也没什么人排队,有个炒饭摊子的小哥就尴尬地炒着空锅。排队多的多是一些local小食,比如dengdeng(大概就是肉脯,老外把它们sweet meat,比如国民肉脯美珍香),炸圈炸串,各式烤肉做的汉堡、kebab、三明治、大饼卷一切。我看到了费城奶酪牛排三明治。我想起离开上海前一个夜晚我在训练馆里和一个好朋友分吃一个费城三明治的情景来:两人都是吃货又都得控制体重备赛,对着美团上的图片流了半天口水,抠抠索索买了一份6寸的撕成两半吃了。可真是太香啦。我俩吃完了还对着锡箔纸意犹未尽。这几天上海还封着,前几天她还在群里说,想吃费城三明治。我看到这个,就拍了照片视频发给她。
牛肉在铁板上烤着滋滋响,缓缓从红色变成铁色,旁边奶酪酱浇在三明治上,真是不能更好。我迫切地想分享给我那爱吃费城三明治的小朋友。她前段时间说她哭了一场,因为这破时事,他们夫妻俩失去生活来源,夜不能寐,想着上海怎么变成了这样。
往前走几步我又看到了在芽笼士乃也看到过的肉食主义狂欢摊(我自己瞎起的名字),看来这是个连锁品牌,标准的羊排、鸡腿、牛肋骨排、汉堡排。

我原不爱在巴扎喝饮料,因为大多数只是为吃肉的搭配,并无多少惊艳的商品,更何况里面不乏加了各种色素的廉价小冷饮,看上去就不想喝。但一个卖甘蔗汁的摊子还是吸引了我,里面好像还放了柠檬和话梅,看上去是一副“比普通甘蔗汁好喝”的样子。一个小哥不停地榨汁,另一个小哥不断地把榨出的甘蔗汁封杯,码在冰块堆里,冰块堆里的新鲜甘蔗汁不断地被涌过来的人流挟裹带走,带到他们自己的人生里去。

这大概就是供应链的魅力,新鲜的、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在这之前我也没想过它会这么迷人。它是蔬菜上的水滴,鱼虾的跳,肉铺的砧声,是人间的脉动。
芽笼士乃的巴扎旁边尚有mall,有不少公共餐桌可以供食客带了巴扎买的食物过来吃。这边就难觅了。好在我离家近,买了ramly burger和甘蔗柠檬汁过了个马路就能回家。看着外面泫然欲泣的天空吃了一顿下午茶。ramly burger果然如我预料地难吃,而甘蔗汁也确实惊艳,话梅是点睛之笔。接过甘蔗汁我指着它问小哥,这是啥?小哥含混说了个听起来很复杂的词,我也没听明白,耸耸肩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