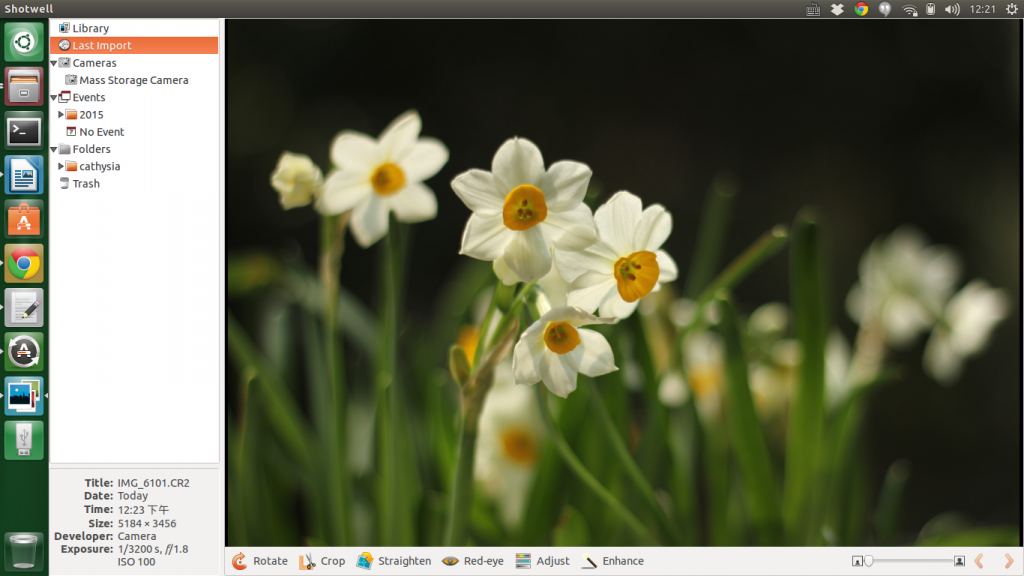昨天晚上有一阵,感觉到极度的抑郁——这么说其实不准确,而是极度感觉不到快乐,心空落无所依,为未来设想的任何可能性都无法调动积极的情绪,过去的快乐回忆又极容易产生悲伤。而对死亡的恐惧又令我产生怎样也无法有妥善解决方式的感觉。
怎样都不舒服,好像是缓缓陷入泥潭。不知道是不是抑郁。求生的本能令我伸出手来求救。跟朋友计划出游,去大洋山,去南法,去印尼,才算透出一口气。
彼时我在外高桥,空无一人的停车场。工商银行的数据中心彻夜通明,Kingston的LOGO发出明亮光芒,凸月悬挂高空,我无所遁形。
其间Karlan发来一张我今年年初在古北的一张照片,说给我的画像部分参照了这一张,他觉得最好看。那时候的我是典型的我,无知狂妄又快乐。总是兴致勃勃不知疲倦。

我回复道,Elle est morte.
Karlan不再说话。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真心地难过。因为我确切地知道,新的蛐蛐未必坏,她懂得了恐惧和珍惜,知道了起点和终点;但这个我最爱的蛐蛐,无知狂妄又快乐的蛐蛐,总是精力充沛的蛐蛐,再也不会回来。
上上周心理医生叫我想象如果生命还剩一年,会去做什么。我简单地答,见朋友,把小说写完。
如果生命还剩半年呢?答:见朋友,把小说写完。
如果生命还剩一个月呢?答:见朋友,写点东西,可能小说写不完了。
如果还剩一周呢?答:见朋友,写东西。我尽量缩短语句,因为已经感觉到自己哽咽,随时有可能哭出来。
上个月最难过的几天里,有好几个下午,在看程浩留下的文字。这个在病床上和死亡脸贴脸睡了二十年的少年说,“……但是我必须坚持写作这个行为,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身上的伤痕变得毫无意义。”他提到了“意义”,看到这两个字,那段时间一直在痛苦思索人活着的意义的我开始停止思考这个问题,接受了“有意义”这个预设。
心理医生这一番问话也令我明白一些。多年来我保持着读书和写作的习惯。我固然希望自己成为学问家、作家,但读书和写作并非为这目的,而是这过程令我安宁。
无知的快乐已经不再,希望我还拥有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