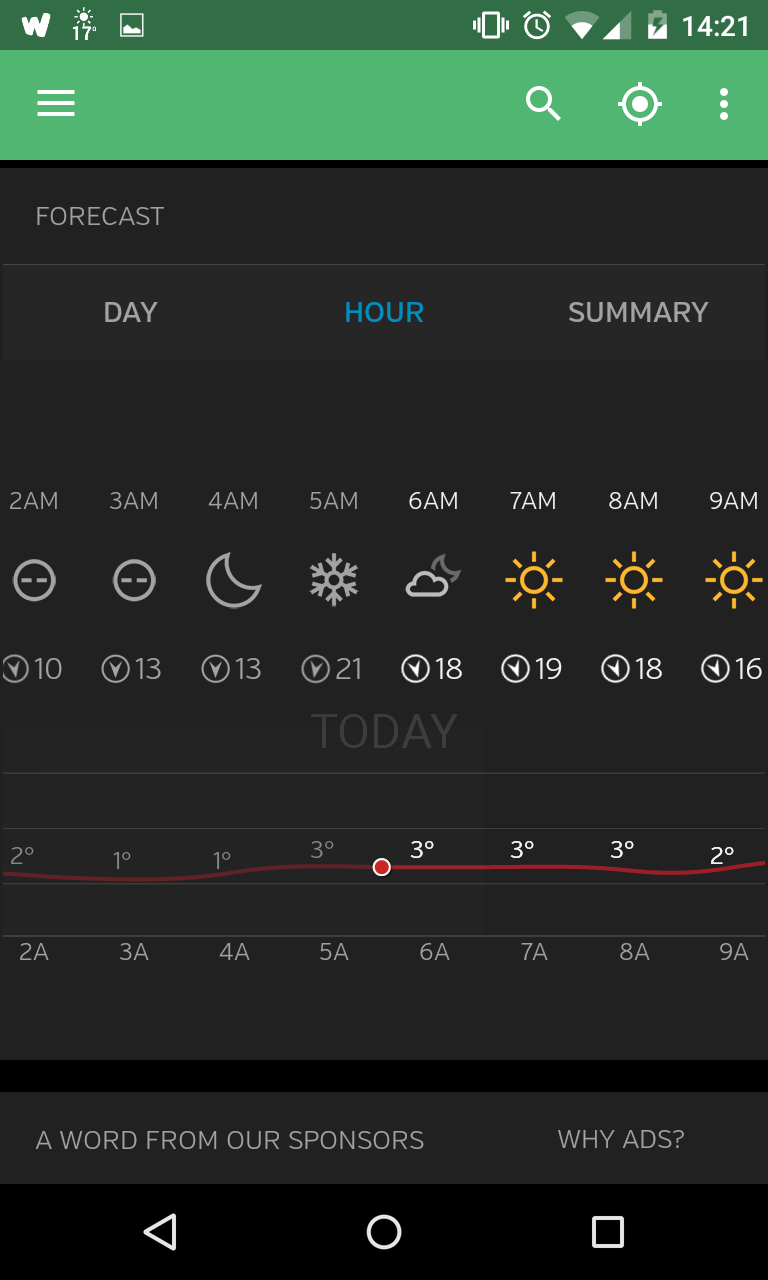去年春节长假,翻译了一本小书。今年春节长假的计划是看完A Byte of Python。
长假已经结束,这个任务只完成一小半。再拖延一个月吧,在这一个月里尽量看完,然后开始一些简单的实战练习。
法语仍旧进度奇缓但从未停下。语言学习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Remi去韩国之后我还没有找到新的法语老师。我并不需要一个专业的语言教师——我自己就是一个二语习得专业工作者,在语言学习计划的制定和语言系统内化的过程我可以自己搞定。我需要的是一个native speaker。Remi就是一个典型的sample——母语法语,并没有语言教学经验。所以一般课堂上是我主导,他更像一个陪读。这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有时候我觉得很累也有点委屈。为什么我教学的时候是我主导,我做学生的时候也是我主导!真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一个比我更牛叉的语言教师,我可以放松下来全身心投入学习,而不是主导课堂。
假期最后几天才一拍脑袋想起,啊呀,盱眙近地天体巡天望远镜的资料忘记搜集了,真是低效啊。
昨天和Ashley去看了敦煌展,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我已经习惯了去人少的地方,摩肩接踵的感觉真糟糕。不过这个敦煌展倒确实令我回忆起不少往事。我的毕业论文。在敦煌的旅行。我和麦扣说起,还想去一趟敦煌,把河西四郡全部去一趟。麦扣也去过敦煌,去过敦煌的人,都爱敦煌吧。
于是,假期这么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