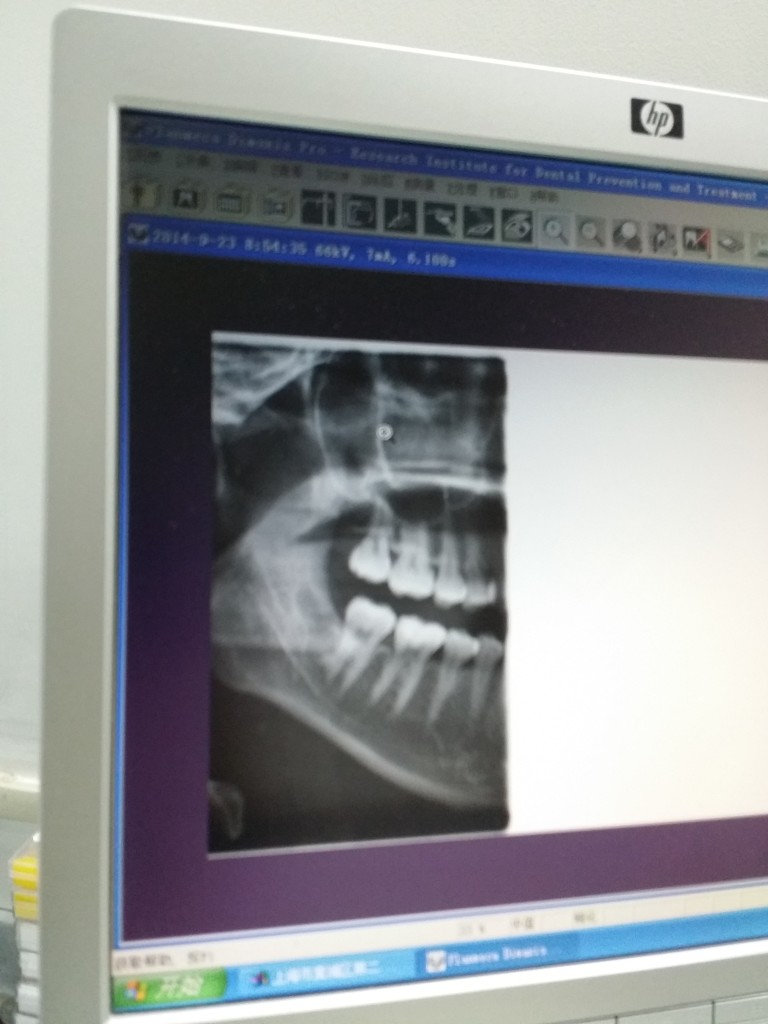接上篇《最后一颗智齿》
卢湾区牙防所在卢湾区并到黄浦区以后,就更名为黄浦区第二牙病防治所。到那里去要经过日月光,那里有超级多好吃的。周六我去那里预约拔智齿,排了号以后就回到日月光,在最爱的翠华吃了一份最爱的鸡饭。这份鸡饭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因为预约过后我顺便把三颗浅龋也补了。这是我童年换牙后第一次补牙,我以为时隔二十年之后医学迅猛发展,医疗过程已十分人性化,不会重演小时候的补牙疼痛和恐惧。
结果是我太天真了。
说来也巧,这次预约和补牙的医生还是上回的那位。不苟言笑的中年男人,对我躺在牙椅上痛得手舞足蹈和嘴巴流着口水还问东问西不以为然。半小时以后我眼泪汪汪地站起来跑了,我讨厌牙科医院的电钻。
过几天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拔智齿。一想到拔完以后我就会成为一个wisdom tooth-free的人,我就满怀憧憬。虽然被告知要开刀缝针,但那又怎样呢,反正有麻药的。预约的时候我忧心忡忡地问医生,会用锤子敲么?医生说,能不用就尽量不用咯,怎么,难道你被敲过?我说,我的前三颗智齿都是被锤子敲掉的啊。医生遂从口罩上方同情地瞥了我一眼。这一眼神令我十分心安——锤子敲我也没觉得有多疼,开刀大约还要轻松些吧。
我还是太天真了。
当天我去得很早,还是等了一小会。交钱,拍片,第一次看清这颗顽固的智齿,长得原来像麻将一样——和其它拥有细长健壮牙根的正常牙齿截然不同,它的牙根是一大坨的。我进诊室以后一个小伙子刚从牙椅上坐起来,捂着嘴巴做沉思状。医生叫他去旁边坐坐,觉得好一点了就可以走了。然后叫我躺上去。
医生给我打了麻药后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划开了牙龈,然后开始了漫长的挖墙脚工作。医生说我的牙根比前面那位小伙子的还要难拔——有两个牙根且带钩。他一边说一边抱怨把两个难拔的智齿都放在一起了,眼看他要累死了。他费力地用工具撬那颗智齿,撬一会歇一会,我忍不住笑起来,他也忍不住笑了。
过了一会智齿被撬了下来,我听见智齿掉在盘子里叮啷一声,心情大好,口腔里弥漫的血腥味也不是那么讨厌了。医生开始弄线来缝针。我看他像西游记里的唐僧给孙悟空缝虎皮围裙那样耐心地穿线,一不留神看见了那个针,是一个黑色的钩子。立刻我整个人都不好了,赶紧把视线投向别处,我没看见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
不过我的噩梦还是来了。麻药的药力不知什么时候褪了下去,第一针下去的时候感觉无法形容——这是我第一次被缝针,实在找不到可以形容的喻体。我痛得哇哇叫起来,医生还是像唐僧缝虎皮围裙一样慢条斯理的,叫我不要叫,说着把针从另一边抽了出来,带出一根长长的黑色丝线。他又说,这才第一针呢,至少得缝两针。
然后他又开始第二针。钢针穿肉的感觉真是无可名状。我的眼泪冒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缝针啊,为什么就没有麻药。
最后医生终于说,好了。把手套摘下来反套在智齿上,塞给我,然后开始背过身去开始写病历,对我说,起来把血吐掉吧,下周来拆线。
我捂着半边脸出了诊室,候诊室里所有人都同情地看着我。我猜刚才我哇哇叫的时候他们全听见了。我后悔自己早晨没有吃早饭就来拔牙了——我总觉得吃了饭去看牙医很没礼貌——我痛得头昏眼花,不记得是怎么坐上地铁回去的。但我并没有忘记路过日月光的时候在食之密买两块蛋糕,一块红桑子,一块夏威夷果仁白巧克力。医生并未说忌口,我就给自己理由吃点绵软的食物吧。
我一点也没法因为拔了早就看不顺眼的智齿而开心起来,两块蛋糕也不能缓解术后的疼痛和阴郁,吃了两口就放下了。当天晚上开始发烧。饥肠辘辘的我叫了一份海鲜粥,歪着头吃了半碗。
夜里我醒了,烧退了,但我还是醒了,好像不是痛醒的。我觉得我的脸有些异样,我舔了舔嘴巴,然后伸手摸了摸脸,在心里发出一声哀嚎。我的嘴巴,我的嘴巴肿了。排除了伤口造成的原因之后,我觉得我是对海鲜过敏了。我呜咽着,又睡了过去。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照镜子。我看到镜子里有个整张脸略肿、嘴巴肿得盈盈欲破的怪异人形。海鲜过敏是小事,戴上口罩,再去药店买盒息斯敏就好了。难过的是伤口依旧痛,不仅是伤口,整个下颌骨都在忍受钻心的疼痛。
脸慢慢在消肿,伤口情况并未好转,到第二天下午开始出现异味,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意味着可能感染了。
买不到抗生素,我这种三年不生一次病的人又从来不会想到屯抗生素备不时之需。我用了各种办法来阻止厌氧菌的侵袭。比如酒精。直接用酒精漱口显然太过悲壮。我选择了二锅头。
情况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伤口时时有液体流出,下颌骨依旧锐痛。而最令我depress的是,我几天没有正经吃东西,已经快要饿死了。我焦虑地去找那个医生。医生用棉球探了探,嗅了嗅,说,没异味啊。我给你开一瓶替硝唑吧。他让我给他看看我漱口用的二锅头,赞道,你是革命家。
我带着疼痛和替硝唑坐上了进山观测的客车。同行还有一位刚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朋友,我在客运站大厅喋喋不休地跟他说我的症状。突然我觉得嘴巴里好像有异物。我吐出来一看,是一根黑色的丝线。
线……掉了……我对医生朋友说。医生朋友满脸黑线,说,掉了……就掉了吧……
疼痛时时搅扰,山上饮食又过于粗犷,很影响我天(you)文(shan)观(wan)测(shui)的心情。下山后我想反正吃也痛不吃也痛,不如死个痛快,遂去古北吃了一份味道非常正宗的豚骨拉面。那是一份诚意满满的豚骨拉面,太治愈了,我感动得快要哭了。
第二根线也没有撑到拆线那一刻,在拆线当天早晨掉了下来。我如约去医院,跟医生说拆线。医生说好。我又说,线掉了……
医生顿了顿,说,那你躺下我看看。遂又用棉球探查,终于承认,是感染了。回头喊护士,拿麻药,我要清创。
又要打麻药。我吓得坐了起来。医生道,那有什么办法呢,你感染了啊,伤口里面都黑了。
一针麻药过后,医生开始又刮刀开始搔刮裸露的牙槽骨,我觉得自己的心像案板上的一块肉,每一次手起刀落都在心上。刮了几下之后,医生让我吐去血水。我朝水槽里一吐,场面立刻像案发现场一样。我回头有气无力地跟医生说,再加一剂麻药吧,我觉得那个麻药一点用都没有。
遂又加一剂。然而牙床依旧有痛感。医生奇怪道,你是不是平时喝酒的,怎么麻药一点用也没。我说,我不喝酒的。医生又哂笑,那二锅头是怎么回事。我怒道,那是消毒!好吧好吧,医生说着又把我的头按下去,开始了第二轮丧心病狂的清创。
我能听见刮刀在牙槽骨上刮过的声音。刮骨疗毒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的眼泪哗哗的地流。
不记得刮了多久,医生终于说,去漱口。我又吐出一大堆案发现场。然后医生开始往上面堆双氧水,双氧水在我的嘴里产生很多泡泡。我又吐出一大堆泡泡。最后医生在里面埋了一块碘仿和明胶算是结束。
残酷的医生说,下去开药吧。我躺在牙椅上咻咻地喘着气,口齿不清地说,你让我歇会儿……
最后我颤颤巍巍地爬起来,擦着眼泪跟医生说,我觉得你们家的麻药,是拿自来水做的。
医生终于肯给我开抗生素。
清创这种事,这辈子绝对不想来第二次。这以后的几天我就像强迫症一样,吃完东西就进行杀菌四部曲——刷牙、李施德林漱口水、替硝唑漱口液、交沙霉素。有几天替硝唑忘带去公司,就去药店买了甲硝唑代替。甲硝唑把我的舌头漂成了白色……然后漱口水又把它染成了绿色……
下午的时候同事们开始叫肯德基吃,他们在讨论着原味鸡到底哪一个部位最好吃。我的眼泪在心里吧嗒吧嗒地流。我是一个天生的吃货啊,我最喜欢吃东西了,我每次经过牙防所都心怀幻想,以为出来就可以去日月光大吃一顿。可是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吃。太委屈了。
伤口不再有异味,然而下颌骨依旧是无法忍受的疼痛。晚上我走在地铁站里,忍受着下颌骨一跳一跳的疼痛,突然筋疲力竭,想要哭了。这种哭和清创时候流的眼泪是两种。后者万全是生理的,离哭还很远。而现在是真的想哭了。距离拔牙已有三周,我还远远没到可以活蹦乱跳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程度,和我拔牙前的憧憬实在太远了。第一次去牙防所看牙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与周围其他牙病患者迥异,因为我只是拔个智齿而已,拔完后我就可以活蹦乱跳,像一只“切了狼趾的狗”一样了。
我只是拔个智齿而已啊。
我靠在地铁站月台上的墙边,委屈地真的想哭了。这种疼痛太不正常了,从未有过的。回到家以后我想来想去觉得症状颇类干槽症——只是没那么严重。一想到可能是干槽症,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干槽症的治疗方法与清创差不多,同样是搔刮牙槽骨,造成伤口,刺激牙肉萌出。然后埋伏碘仿和明胶,有必要的话还得再缝一针固定。
我万念俱灰地给医生发短信,“我觉得我可能得干槽症了……”很久以后医生回复道,明天来我再看看。
第二天又赶大早去牙防所。今天医生是在四楼的专家诊室里,我对医生说,医桑,今天你变成专家了啊。医生慈爱地说,是啊。然后就把探针塞到了我的伤口里。
万幸的是,不是干槽症。第二天医生看了之后说,没有异味,应当不是干槽症。再给你换一下药吧,国庆之前早晨来换药。不用挂号……算了你还是先挂个号吧,省得有些人要吵……换好药以后我再给你把号退掉。
一听不是干槽症,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下颌骨的疼痛怎么办呢,清创时候拍的牙片现实牙根已全部清除,下颌骨没有什么异样。看来只能忍到它自行消失了。
医生是个不错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给我开抗生素,也没有忌口之类的烦人要求。他看我的脸不肿推测我身体不错,令我很受用。(当然最后还是掉了链子)有次我换药的时候,有个老太太,补完牙发现医保卡里没有钱,讪讪地来找他。他不声不响地把事情解决了。老太太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来和我说,一个月医保卡只能刷两次,你下次换个人的医保卡来刷吧。我换谁的呢,总不能换狗弟弟的吧。后来还是用医保卡去,他就直接把我挂的号退了。
不过我已经产生了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看到他就怕得发抖了。所以国庆前最后一次换药,换好药我说了声谢谢医生假期愉快再见就xiu地跑了。
然而这个国庆,因为疼痛,也没有过得太好。为了庆祝我可以少量吃点固体食物了。Stacey见到我,惊叫道,你怎么瘦了这么大一圈,然后带我去了Shanghai Brewery,吃了老早就像吃的德国猪肘和我最爱的教父汉堡。她叫了一份黄啤,我啜了几口上面的泡沫。然后去Cold Stone吃了一份巧克力冰欺凌。
于是国庆长假第一天,嗓子火烧火燎,第二天开始流鼻涕,晚上发烧,第三天咳嗽。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免疫力降低的缘故,我被这场感冒折腾得死去活来,半死不活地去药店买了白加黑。
说来也怪,几片白加黑和阿司匹林泡腾片下肚之后,下颌骨的疼痛显著减轻了。起初我只以为那是麻黄碱的暂时镇痛作用。但停药之后疼痛也未见疯狂反扑。一时间百感交集。
我也不确定是白加黑的作用还是阿司匹林的作用,还是疼痛到了时间了。无论如何,这是我拔掉的最后一颗智齿,也是折腾我最久的一颗智齿。
这颗智齿和其它三颗太不一样了,首先它并不和其它智齿一样总是发炎疼痛。它虽然长歪了,但总是安静地呆在那里,从来不惹事。如果不是因为角度形成缝隙,容易引发龋齿,我也实在想不到任何理由去遭这个罪。
它现在还血迹斑斑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我不喜欢留纪念,但是也许我可以把它钻个孔穿起来,戴在狗弟弟脖子上。
智齿的复仇,至此应该就结束了吧。